《台灣的命運》作者點評近代人物:曹錕的「賄選」反而證明了他的憨直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曹錕部下付給舊國會議員的津貼,能不能算賄賂,其實完全是個立場問題。議員宣稱,這是他們應得的辦公費和差旅費,而且根據他們自己制定的標準,他們本來應該得到更多。
文:劉仲敬
曹錕(1862-1938,天津大沽口人)本是毅軍哨官,在馬玉昆[1]的遼東戰役後投奔袁世凱。毅軍是甲午戰爭當中沒有崩潰的少數淮軍分支,後來又參加了庚子戰爭,表現都不像特別精銳的部隊,但以打不散的團結性為特長。
馬玉昆當時是沙場宿將,袁世凱則是銳意革新的局外人。年輕的曹錕以忠厚和勤勉著稱,卻很少有人讚賞他的遠見卓識。他這次選擇如果是為了尋找能夠破格用人的東道主,本來是頗為明智的,然而他當時的動機似乎更像出於私人交誼,而且在小站(按:天津下轄一鄉鎮,袁世凱曾在此練兵)也沒有急於上進的跡象。
他慷慨大方但近乎濫好人,除了特別難伺候的角色,幾乎是每個人的朋友。他的升職是緩慢而有條不紊的,跟他的性格很相似。他用人不疑、有財不貪、有功肯讓,因此頗得軍心,但在刻薄人的眼中,也可以解釋為能力不足。辛亥戰役證明這種說法不太正確,因為他指揮的太原戰役是民國初年少有的歐洲式正規戰。南北議和,第三鎮(後來的第三師)返回京畿。他們的譁變迫使袁世凱留在北京,召集張家口的姜桂題[2]入關平亂。
鑑於第三師是北洋的核心,而姜桂題乃是「毅軍」鮑超的舊部,要外圍得多,所以曹錕在幕後扮演的角色引起了眾多猜疑。
第三師在二次革命中為袁世凱擊潰了湘軍,卻未能在護國戰爭中擊潰滇軍。隨著曹錕地位的上升,第三師交給了吳佩孚。曹錕的後半生事業,跟吳佩孚難以區別。二人既有性格的互補,又有價值觀的契合。
曹錕喜歡說自己是大帥,吳佩孚也是大帥,有功勞要分給部下,栽培部下做大帥。吳佩孚則以關雲長侍劉皇叔為榮,自詡不以成敗利鈍為轉移的忠臣。直皖分裂、直奉分裂大半是吳佩孚勇往直前的結果,直系最初的勝利和最後的失敗,吳佩孚的冒險主義都要負最大責任。
而曹錕都是直到最後關頭才不得不改變妥協的初衷。然而如果沒有曹錕,直系能不能存在都成問題。吳佩孚自始至終遭到直系其他將領的厭惡,需要曹錕出面斡旋。如果沒有曹錕,他更有可能淪為馮玉祥式的孤將,而且還沒有馮玉祥的機會主義手腕,大概會在歷史上轉瞬即逝。
曹錕留下的最大爭議在於所謂的賄選,但此事與其說證明了他的敗壞,不如說證明了他的憨直。
他不願做名不正言不順的僭主,堅持追求合法的名分。這種天真的感情其實就是法統的力量所在,正如妻妾有別的迂腐才是婚姻的力量所在。法統的敗壞出自相反的原因,也就是只認實權不認正統的馬基維利主義。
曹錕部下付給舊國會議員的津貼,能不能算賄賂,其實完全是個立場問題。議員宣稱,這是他們應得的辦公費和差旅費[3],而且根據他們自己制定的標準,他們本來應該得到更多。如果你承認舊國會本身的合法性,這裡面就只存在適當不適當的問題,因為財政權永遠都是國會專屬的特權。
如果國會認為五千大洋還不夠支付天南海北的辛勞,那麼給實際出席的議員另發五萬大洋的欠條都在他們的權限之內。如果你不承認舊國會本身的合法性,就應該連他們非法占據議事堂期間的租金和茶水費一併追討。
何況有一點可以肯定,1923年國會會議科的支付[4]用於交換議員的出席,而非投票[5]。議員只要出席就能領到支票,投票卻是祕密舉行的。支持曹錕的主流派只擔心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不擔心得不到多數票,甚至致電國民黨議員,請求他們前來投孫文一票[6]。
如果這筆錢的性質可以定為賄賂,賄賂的目標也不是為了擁戴曹錕,而是為了爭取分散在各省的議員返回北京。北京看守政府通過國會會議科付給出席議員的五千塊錢,能在1913年制定的《議院法》中找到依據。孫文—段祺瑞—張作霖「三角聯盟」通過楊宇霆和盧永祥的私人途徑,付給不出席議員的五千到一萬大洋,似乎更加缺少法律依據。
賄選問題如此沸沸揚揚,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反直系勢力的幕後活動。後者無疑希望借助宣傳手段打擊曹錕,卻沒有理由在各種攻擊手段之間厚此薄彼。如果他們寧願發掘在法律上並無充分依據的賄選,卻放過了在憲法和法律上都是證據確鑿的驅黎(元洪)兵變,那很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普遍具有畸形的價值觀,對賄賂的敏感性高於強暴。
從憲法上講,舊國會和黎元洪大總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要麼兩者都合法,要麼兩者都不合法。兩次法統重光,舊國會的恢復都自動導致黎大總統的復辟。舊國會居然坐視直系軍人趕走自己選舉和召集自己的黎大總統,然後宣布自己仍然有合法權力選舉黎元洪的敵人為黎元洪的繼承人。這種怪事的荒謬之處猶如妻子坐視強姦犯趕走了丈夫,然後覺得自己有權為強姦犯舉行一場合法的婚禮。
賄選的指控者比他們更荒謬,不去追問強姦犯有沒有資格補辦婚禮,卻要大肆鼓譟說鑽石戒指給這場婚禮帶來了買賣婚姻的嫌疑,彷彿女人「貪慕錢財嫁人」是件很了不起的罪行,比「協助強姦犯占據親夫的家業」嚴重得多。
在細枝末節的程序問題就足以引起內戰的時代,如此根本錯謬的理解居然能夠構成敵對各方的共識,既奇怪又理所當然,既可悲又公平合理。他們,或者不如說我們,通過這樣的手段,在隱祕的世界法庭上,為自己下達了這樣的判決:天下可以搶到,但不能買到。如果你搶到天下,就有權自稱擁有天下的愛戴。如果你買到天下,就無權冒稱擁有天下的愛戴。晚期羅馬的禁衛軍和晚期埃及的馬姆魯克(Mamluk)[7]擁有完全相同的共識,他們統治的對象同樣是極其墮落的文明餘燼。
Tags:
一圖看懂史上最超值 5G 手機 moto g34 5G,台灣大電信獨賣無痛升級 5G 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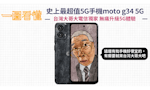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Motorola 最近與台灣大哥大聯合獨家推出 4 千元有找的新機 moto g34 5G ,光看手機型號,不難猜出這是一支 5G 手機,而且還是史上 CP 值最高的 5G 手機,搭配台灣大哥大 5G 專案,月付 599 元就能以 0 元帶回家,可說是任何人升級 5G 體驗的首選!
5G (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自從 2020 年 6 月底開台,距今已上路將近 4 年,若你還堅守 4G 遲遲未換機,可能基於 5G 手機選擇少、或用不到 5G 高速上網等理由。不過,隨著 5G 手機逐漸普及,加上各種高畫質影音串流,開始對下載速度有一定要求,現在也該是時候升級 5G 了。然而,大家對 5G 手機的印象,多半停留在規格高、價格昂貴等刻板印象,但其實市面上早已出現許多平價 5G 手機了。
以歐美手機大品牌 Motorola 為例,近幾年推出 motorola razr 40 系列高階 5G 手機,尤其採經典的摺疊機造型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實 Motorola 也有顧及入門市場。最近與台灣大哥大聯合獨家推出震撼市場的超平價 5G 手機 moto g34 5G ,不但空機只要 NT3,990 ,搭配台灣大哥大專屬 5G 專案,只要月付 599 元,就能以 0 元直接帶回家,堪稱為地表最超值的 5G 手機,適合家中長輩、孩子,或任何對 5G 感興趣的人無痛升級 5G 。

moto g34 5G 入門機新登場 同價格帶 5G 手機最佳選擇
何以說 moto g34 5G 是 CP 值最高的 5G 手機?最關鍵點當然在於 5G,5G 網速最快可達到每秒 10GB ,光是以網速來看, 5G 比 4G 快了 100 倍,這 100 倍差異會表現在哪?例如觀看 MyVideo 之類的線上串流平台,就算把影片切換到最高畫質,也幾乎不會感到有延遲;或是小朋友用來玩線上遊戲, 5G 高速傳輸讓畫面不卡卡、並確保任何指令都在彈指之間完成。

5G 對長輩提升手機體驗也有幫助,例如老人家每天最愛 LINE 來 LINE 去,但如今多媒體檔案愈來愈大,無論是網路下載、或自己拍攝的影音檔案動輒幾百 MB ,若是透過 5G 速度傳送或接收,肯定能省下更多寶貴時間。過去要享受這些 5G 高速體驗,至少要花萬把塊升級 5G 手機、或是綁貴鬆鬆的費率。不過 moto g34 5G 把「 CP 值」發揮到極致,為市面上罕見不到 4 千的 5G 手機,且搭配台灣大 5G 專案,月付 599 就能以 0 元帶走,不但不用花太多錢買手機,每個月也只要付少少的月租費,就能享受 5G 高速上網帶來的好處。
6.5 吋大螢幕、 120Hz 更新率、 Dolby 立體聲喇叭、流暢無比的影音體驗
雖然空機便宜、專案價付得輕鬆,但可別以為 moto g34 5G 是支陽春手機,其實規格或功能都在水準之上,以下就看我們開箱介紹。首先看看外觀, moto g34 5G 搭載 6.5 吋超大 LCD 螢幕、解析度為 HD+(1600×720) ,比較特別的是支援 120Hz 螢幕更新率,無論用來播放影片或玩 game ,都能呈現流暢無比的畫面,除了是 5G 手機、更是一支稱職的影音手機。

雖然定位為 5G 入門機,但在機身質感的處理, moto g34 5G 可是一點也不含糊!
照片中的孔雀綠款,可見到機身背部以高質感素皮材質處理, moto g34 5G 還提供黑色款,同樣把極致的黑色融入金屬噴漆外框與玻璃般的背板,兩者皆營造出令人驚艷的視覺效果,非凡的質感、加上極佳的手感,讓人誤以為 moto g34 5G 是高階旗艦機呢!另外還有限量的冰晶藍,大家可以親自入手體驗看看!


其他細節部份, moto g34 5G 機身兩側分別為 SIM 卡槽、電源與音量調整鍵,底部則有 Type-C 孔、 3.5mm 音源孔與 Dolby Atmos 立體聲喇叭;值得一提的是, moto g34 5G 還搭載 microSD 記憶卡插槽,最大可額外擴充 1TB 儲存空間,為愛拍照與錄影的使用者,提供儲存影像所需的大容量。


入門機規格不含糊、搭載多項貼心功能、夜拍體驗再升級
接著看看 moto G34 5G 內在功能,硬體規格配置為 Snapdragon 695 5G 八核心處理器、 4GB RAM 與 64GB ROM 記憶體,其中RAM還支援擴充技術,最大擴充至8GB,有效提升運行效能和多工處理能力,提供更好的使用體驗。採用最新 Android 14 作業系統,無論是主頁面或程式清單,整體介面設計簡簡單單,無論是愛瘋跳槽新用戶、或是安卓舊用戶都能秒上手。

雖然定位為入門 5G 手機,不過 moto G34 5G 內建許多實用功能,例如能將手機畫面轉移至大螢幕上的 Moto Connect ,或是可控制應用程式權限、掃瞄手機是否有病毒,使數位生活更加安心的 Moto Secure。至於電力部份, moto G34 5G 內建 5,000mAh 的大容量電池,支援 TurboPower 18W 快速充電。

最後看看拍照功能, moto g34 5G 搭載 5,000 萬畫素主鏡頭與 200 萬畫素廣角鏡頭,除了有貼心的補光燈設計,另外還支援 Quad Pixel 技術,在低光環境下感光度提高了 4 倍,確保拍攝出更清晰、更生動的照片。至於前鏡頭則是 1,600 萬畫素,超高解析度讓使用者可盡情自拍。


附上幾張實拍照給大家參考,由於 moto g34 5G 特別強調能提高夜拍效果的 Quad Pixel 技術,以下實拍照以夜拍為主,大家不妨可用肉眼感受 moto g34 5G 的拍照實力。


moto g34 5G台灣大哥大獨家開賣 搭配指定資費方案手機 0 元起
看完本篇實測,相信大家對 moto g34 5G 非常心動吧!既然遲早都要升級 5G ,何不把握這次 moto g34 5G 升級 5G ,搭配台灣大指定5G資費方案月租 599 元,手機 0 元就能帶回家,輕鬆享受台灣大哥大全台最大5G黃金頻寬,還有獨家HBO GO、Disney+、KKBOX、MyVideo等多重影音娛樂優惠,最後附上資費方案表格給大家參考。










